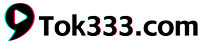责任编辑: cixianw.com
【编者按】⼈物专题 「灵感之乡」 ,聚焦具有启发性的思考与实践。我们探访不同领域的践行者,记录他们的思考如何落地⽣根,并发展成为打动⼈⼼的经历。
半个多世纪前的一个冬日,英吉利海峡,一位10岁的法国女孩近乎半冻僵地站在一艘帆船的甲板上,着迷地看着泽西岛(Jersey)海岸外雪花落入海中、与海浪融为一体的景象。她发誓有一天要独自环绕地球航行,冒着寒冷和大雪的天气向冰冷的南冰洋(Southern Ocean)进发。
那个女孩就是伊莎贝尔•奥蒂西耶(Isabelle Autissier)。我们在她选择的午餐地点——“4名中士”(Les 4 Sergents)餐厅门口碰头。这家餐厅靠近她位于大西洋的港口城市拉罗谢尔(La Rochelle)的家。她告诉我,她已经完全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愿望。如今那些关注航海的人,一眼就能认出她那一头凌乱的卷发和苦笑。
她已四次环绕地球航行,而在成为法国--这个对于单人航海最为狂热的国家--最知名女运动员之一的过程中,她屡次打破纪录,成为第一位在竞赛中独自环球航行的女性,并有两次在南极附近的惊涛骇浪中获救的经历。如今,她是一位知名的小说家、广播节目主持人和环保主义者,致力于保护她在儿时所神往的海洋。
她仍然经常在偏远的极地海域航行。“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开始思考海洋,自那以来,海洋一直是我生命的主轴。航海占据其核心位置,”她说道。我们在餐厅优雅的玻璃和金属天篷下就座,玻璃和天蓬都是当年由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的工场制造的。这个地方以前是个花园,如今是餐厅。(餐厅名称中的四中士是1822年被送上断头台的波拿巴分子,传说其中两人曾短暂逃离位于附近的灯笼塔(Tour de la Lanterne)的监狱,并藏身于此。)
我有很多问题要问奥蒂西耶,不仅是关于她的航海壮举的问题,还想问她作为一名作家(她甚至写过一部歌剧剧本)以及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领导者的生活,她曾说我们的星球应该被称为海洋,不是地球。但是,我自己作为一名胆怯的水手,必需了解她在南冰洋的经历:有一次,她和失事的船一起等了四天,才被澳大利亚海军直升机救起;在另一场竞赛中,她幸运地被另一名航海家乔瓦尼•索尔迪尼(Giovanni Soldini)发现,然后从倾覆的游艇下救起她。1997年时,加拿大船长格里•鲁夫斯(Gerry Roufs)在旺代单人不靠岸航海赛(Vendée Globe)中遇难,当时狂风巨浪掀翻了他的船,而奥蒂西耶无法找到他。
奥蒂西耶对她的翻船经历态度淡定,对死亡的可能性也就事论事。“没错,我已经两次陷入这种处境,但这些事情确实是可能发生的。第一次,我的桅杆断了,于是在凯尔盖朗群岛(Kerguelen,印度洋南部一群岛,隶属法国海外领地法属南方和南极领地——译者注)停靠,在搭建了一根临时桅杆后再次出发,结果在巨浪中翻了个底朝天。
“那艘船彻底被毁了,船舱顶部被整个掀掉了。但两次我都或多或少有同样的感觉。我没有恐慌——我这么说不是为了……我只是在一瞬间变得务实。当我的船第一次翻滚然后正过来时,我看到它已严重进水。我拿一只桶把水倒空。然后我开始思考,我该怎么办?就在那时,我发射了求救信号。
“我想我还是很乐观的。我的心态是解决问题。如果有问题需要解决,你就解决它。如果你不去解决,那么生命总有一天会结束。晚结束比早结束好,但也就仅此而已……当你在航海时,你总是会思考2小时、6小时、24小时后会发生什么,而且你会考虑A计划、B计划和C计划。如果这些计划都不起作用或者失败了,我该怎么办?你有一种心态机制,帮助你做好心理准备。”
我说,这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船长。我们开始享用开胃菜。奥蒂西耶点了胡桃南瓜汤,而我要了一份蟹肉开胃菜,带有一丝芥末的味道。我们完全沉浸于交谈,而她对美食的态度就像对航海与死亡一样就事论事。
当我鼓励她按照“与FT共进午餐”的传统、点评一下她的菜时,她简洁地用一个词“美味”来形容她点的汤,但提到她曾经吃过一顿“盲餐”,而那段经历证明了当你看不见自己在吃什么时,要分辨出胡萝卜与土豆有多么困难。她对葡萄酒的看法更为强烈一些,很快为自己点了一杯布尔格伊(Bourgueil)红葡萄酒,并对我的选择——来自旺代(Vendée)当地的白葡萄酒——发表了评论:“它们现在好多了——15年前它们很糟糕。”
---
经过好几个月的安排,我们才在这个细雨纷纷的冬日在拉罗谢尔吃上这顿午餐,因为奥蒂西耶似乎总是在航海。她刚从法属波利尼西亚的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回来,但她暗示,这次航海太轻松、太舒适了,不是她喜欢的那种“具有挑战性”(她用了challenging这个英文词)的探险活动。
那么接下来她要去哪里呢?现年66岁的她已经放弃了单人竞赛,而更喜欢与科学家一起从事“绝对自由的”探索(她最初研究甲壳类动物,当年作为渔业研究员来到拉罗谢尔),并帮助艺术家和登山者去那些没有机场或道路的险恶之地。
“我做我想做的事,去我想去的地方,与我想合作的人一起,”她说。如今,她自己的船不再是一艘轻型竞技帆船,而是一艘坚固的铝质游艇,不依赖于企业赞助商,她将其比喻为一辆具有越野性能的“海上山地自行车”。船在冰岛,她下一次航海的目的地是格陵兰岛。
奥蒂西耶在巴黎地区长大,在父母的引导下接触帆船运动,父母拥有小艇和一艘龙骨船,后者由她的父亲与16个合伙人共同拥有,这种安排是为了降低成本并让船能在全年航行,而不只是典型情况下的夏季两周。
“我父母是环保主义者,远远超前于他们的时代,”她笑着说道。“小时候,我很快就厌倦了洋娃娃。反而,我很喜欢工具箱。”20岁出头的时候,她买了一个“像生锈的浴缸那样”的钢质船体,然后在拉罗谢尔的旧仓库区打造自己的游艇。她辞去了工作,与朋友一起出发前往非洲和巴西,然后坚持要独自一人从加勒比海穿越大西洋返回法国。她迷上了航海。
这一切对一个以航海为乐趣的业余爱好者来说是说得通的,但为什么会有冲动要去北极与南极附近那极端且冰冷的高纬度海域呢?她耐心地向从未亲眼见过冰山的我解释,首先是令人惊叹的陆地景象,以及极光的角度及其未受污染的清澈。其次是冰天雪地和未受破坏的美丽风景,还有那里的野生动物看到人类毫无恐惧,不像其他地方的动物那样会逃跑。
最后,对于一位成就卓著——包括打破19世纪从纽约绕合恩角(Cape Horn)到旧金山的淘金热航线的速度记录——的女性,存在一种克服挑战的渴望:“这更好玩。海图是错的,所以你会置身于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陌生海域……就导航而言,这非常令人兴奋,是一种神奇的经历。”
我心里想着,这听起来也是又冷又可怕,但接着把话题转向她作为一名成功小说家的第二职业。在最近几周为了准备与她共进午餐,我读了她的几本书,我提出,她笔下那些坚强、孤独的女性角色就是以她自己为原型的,比如,在去年出版的关于一场气候相关灾难的未来主义故事《威尼斯沉没》(Le Naufrage de Venise)中年轻的生态活动人士莉亚(Léa);或者是她迄今最成功的小说、讲述一对被困在一座废弃捕鲸岛的航海夫妇的《突然孤独》(Soudain, Seul)中的路易丝(Louise)。
“有人建议我写女权主义小说。嗯,那个想法很好,但我没有……”。她停顿了一下,我提出,她没有刻意渲染女权主义。“确实没有,”她表示同意。“例如,我在《突然孤独》中有点刻意去做的就是试图不落入陈词滥调,即男人勇敢地面对自然,解决问题之类的。”
“从小说的角度来看,让这位表面上身体虚弱的年轻女性成为主角更有意思……而在另一方面,为什么不呢?看看当今世界上的女性,她们中的许多人具有非凡的勇气和坚韧,而且往往是那些资源最少的女性、没有钱的女性,到头来还要独自带孩子。在我看来,这不是遗传,而是文化。与男性相比,女性往往会陷入更艰难、负担更重的境地。”
她自己没有孩子,但很喜欢她的六个侄女和侄子,并且曾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男子的伴侣。她并不后悔自己在生育年龄投身于环绕世界航海。“我有一些朋友深深地被为人之母所吸引,她们想要怀孕的经历,但这些从来没有真正吸引我。”
至于以女性为主角的现代版《鲁宾逊漂流记》故事《突然孤独》,该书已经或正在被翻译成10种文字,并将很快被拍成一部电影。而她喜欢尝试新事物。前一阵有一天,我看到她在巴黎一家小剧院的舞台上讲述海洋的故事。她还与她的音乐搭档帕斯卡•杜库蒂乌克斯(Pascal Ducourtioux)创作了一部“有点古怪”的气候主题歌剧《健谈的人》(Homo Loquax),由法国广播电台(Radio France)录制成广播剧,并在几个地方剧院演出。剧中,人们几个世纪以来使用的词语从融化的冰盖释放出来,然后飞回它们第一次被说出的地方。
---
我们的午餐是典型的法式两小时午餐,但我们在主菜上进展快速——她点了一份素食拼盘配意大利调味饭,我点了一份相当耐嚼的烤鮟鱇鱼(我本应记得鮟鱇鱼就是这样的)——在我们喝咖啡之前,我想问一下她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的生活。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航海家们经常转向环保事业——英国的艾伦•麦克阿瑟(Ellen MacArthur)和她发起的反对塑料垃圾的运动就是一例——刚开始阅读《威尼斯沉没》时,我担心该书会是一篇愤怒的环保主义宣传品勉强伪装成小说,结果却发现,尽管气候信息明确无误,但这部小说的情节设计得很好,人物也很能引起共鸣。在威尼斯灾难中幸存下来后,精力充沛而孤独的莉亚与唯利是图的政客父亲仍然不来往,而是独自在本土面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她会成为一名气候活动人士,也许你会看到她向名画丢几罐蛋黄酱,”奥蒂西耶笑着说。
和我一样,奥蒂西耶感到困惑的是全球变暖——她从北极和南极的冰盖融化看到了这方面的证据——竟然变成了一个引发分裂的政治问题。气候变化否认者把变暖现象视为一个信仰问题,而不只是我们需要应对的现实。她想知道,为什么只有乌克兰战争才说服了欧洲人节约能源,并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我很悲哀地说,我们必须受苦才能不再是白痴。我宁愿我们愚蠢的时间越短越好。”
“关于威尼斯(以及海平面上升),我问自己的问题之一是关于否认的。为什么我们完全否认人类现在的处境,以及人类将要陷入的处境?情况并不是我们不掌握事实。40年来,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一直在告诉我们一切……事实是非常清楚的。”
她补充说,将可持续发展视为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一种平等互动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现实更像是一个多层的蛋糕,地球及其物理功能在底层,其他一切都在上层。如果你破坏了环境,那么其他一切——包括人类社会——都会崩溃。
谈到乌克兰使我们把话题转向寒冷的童年住所,以及战前我们的父母那一代要如何比他们的子孙节俭得多,我们还谈了甜点。她点了酸橙布丁,而我点的三样餐厅自制的沙冰——无花果、红果和梨——无疑是我选择的最好的一道菜,接近佛罗伦萨维沃利(Vivoli)冰淇淋的那种完美。
喝咖啡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们在彼此间没有争论任何事,而是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看法相同——夜间航海和仰望星空的喜悦、更喜欢纸质海图而不是电子海图、英国退欧的愚蠢、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尽管发表了很多演讲,却未能作为一名注重环保的法国总统被载入史册——所以,我回到关于海洋乃至整个地球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可以做些什么来拯救它们?
“当今的问题在于缺乏科学文化,缺乏与自然的接触。当你置身于自然世界时,你可以随便发表意见,但最终要由大自然说了算:冷就是冷,热就是热,无论那是不是适合你。于是人们总是到虚拟世界中去寻求庇护,过着虚拟的生活。这一切意味着缺乏理解,缺乏严谨,我们最终得到的是情绪和各种各样的废话,以至于人们竟然认为,一个做了30年研究的物理学教授的观点并不比邻居的观点更能站得住脚,后者走到外面说今天很冷,所以不可能有任何全球变暖。”
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的科学家,她选择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她曾担任该基金会的法国主席,现在是名誉主席——作为她的环保工作的载体,因为该基金会专注于科学。“我努力保持活跃。乐观或悲观都不会帮助任何人——这是我务实的一面——所以我宁愿做点什么。这对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助于摆脱苦闷。我已经有了侄子和侄女——我现在甚至已经当上伯祖母了,再看着世界在我们周围崩溃,或者想着那些一直以来的坏消息,真是太可怕了。”
她还能继续航海和从事环保活动多久?“我今年66岁,所以一切都还好,当然,就像每个人一样,总有一天我会不能再做这些事。我估计我至少还有10年多的时间,在那之后,我们就看着办吧。”说完这话,我们道别了,她骑上自行车离开,去为下一次探险做准备。
菜单:
餐厅:Les 4 Sergents
地址:49 Rue St Jean du Pérot, 17000 La Rochelle, France;
胡桃南瓜汤:16欧元;
蟹肉头盘:21欧元;
蔬菜拼盘配意大利调味饭:26欧元;
鮟鱇鱼:41欧元;
奶油酸橙:16欧元;
沙冰:9欧元;
红葡萄酒(Bourgueil Cabernet Franc cuvée Déchainée 2021 Lamé Delisle Boucard)两杯:14欧元;
白葡萄酒(Petit Fagot Sauvignon Blanc Val de Loire Vendée) :6欧元;
咖啡两杯;
总计149欧元。
马凯(Victor Mallet)是英国《金融时报》驻巴黎记者,译者/和风
文章编辑: cixianw.com